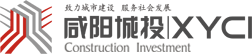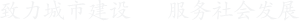资管新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落地后,不少券商资管和基金子公司已经逐渐从融资类业务中退出,而地方融资平台亦在这一轮资管退潮中受到影响。
不少信托公司也在提高政信类信托业务的门槛,且风险关注点也从此前的“隐形兜底”逐步走向对融资平台主体信用的审视。
业内人士认为,以上变化均与管理层对地方举债违规担保、隐形兜底等乱象的整顿有关。
“打破地方债的刚性兑付惯性虽然需要时间,但终究是大趋势;因为不少发安慰函的地方政府都被点名了,所以现在还敢这样顶风操作的平台并不多了。”上海一家信托公司信托经理表示。
对于地方融资平台而言,过去5年间成为其重要融资组成部分的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正在渐渐远离其融资体系。
“现在发资管产品来融资很少了,不发(安慰)函的没人敢做,发了的更不敢做,我们也不敢担这个风险。”东北地区一家县级市融资平台负责人叶青(化名)表示。
叶青所描述的状态,的确是当前资管产品从地方平台融资链条中抽身的缩影。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多家券商资管已经逐渐在地方融资平台等业务上做“减法”。
“主动承担风险的融资平台项目业内基本已经不做了,剩下的几乎都是通道项目。”北京一家券商资管部负责人表示。
在资管新规的嵌套限制下,资管机构为融资平台提供通道业务的空间也在收窄。根据要求,不同资管产品间的嵌套行为最多限定在“一层”。
“以前是银行投资管,再投信托,但是资管新规要求只能嵌套一层,所以券商在结构中的作用也下降了。”前述券商资管负责人表示,“目前只有集合类产品还有嵌套价值,例如我们发集合资管对接集合信托,再投向政信类项目,但这种项目也很少了。”
相比于券商而言,基金子公司对地方融资平台业务的撤退似乎更早。
“从去年开始就不做这个业务了,因为要满足净资本监管要求,而这一类业务不但承受较高的合规风险和信用风险,本身就是有成本的。”北京一家基金子公司负责人表示,“不但增量不做,我们还在对存量的风险项目进行自查排查,并对具有潜在隐患的项目安排风险预案。”
另据记者获悉,一些原券商资管人士正在携带地方融资平台“资源”出走回归信托公司。
例如今年3月份,上海一家券商资管投资经理张华(化名)就在未拿到年终奖的情况下选择跳槽至一家信托公司。
“券商的地方平台业务越来越难做了。”张华表示,“券商和基金子公司不做融资类项目是行业性的问题,所以去信托公司才能继续发挥既有的业务资源。”
事实上,张华此前也曾在信托公司从事政信类信托业务,后于2013年资管行业大发展之际转行至券商资管部门。
“那时候大资管刚开始火热,公司(所在券商)要大力发展类信托业务,也就是政信和房地产类的资管,因为券商也没有这方面的人,所以团队都是从银行和信托公司挖来的。”张华告诉记者,“后来也想过去基金子公司,不过行业政策变化太快了,所以回到信托公司还是比较稳妥的选择。”
在资管模式遇阻同时,此前一度火热的融资租赁模式也受到影响。
其原因在于审计署正在强化对该模式下地方平台违规举债问题的监管。4月审计署公布的《2017年第四季度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结果》中,“通过利用政府道路管网等公益性资产开展融资租赁”就成为部分省市县地区违规举债的一种方式。
“目前一方面是融资结构不好安排,合规要求提高了;另一方面融资租赁公司也比较谨慎,不太敢轻易给地方做项目了。”叶青坦言。
对融资平台来说,其资管、租赁方面的债务一旦到期,也有寻找新渠道来承接流动性压力的刚性需求。
政信类信托被业内视为一种选择。
“本身融资平台就是此前信托的主营业务,因为2012年证监会开放资管投资范围后这些业务才外流到券商和基金公司的。但在监管压力下,信托公司可能仍然是做这类业务的主力军。”张华表示。
虽然如此,但此类信托的数据也在下降。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5月末政信信托余额为1592.60亿,相比上年同期下降近三成。
张华告诉记者,由于严禁政府担保和打破地方债刚性兑付等要求,信托公司虽然具有开展平台类业务的合规优势,但大部分信托公司已提高准入门槛,这也让不少平台融资需求被“拦之门外”。
“现在多数信托公司融资平台业务的准入门槛都在提高,像我们至少要主体评级AA+才行。”张华坦言。
除信托外,发行标准化债券或许也是一条替代出路——资管模式停滞的同时,城投债的发行规模却出现了倍增。据Wind数据显示,2018年前5月城投债合计发行规模达9660.15亿元,同比增长79.57%。
同时,私募基金亦被视为潜在的融资方式。“也在研究通过私募基金进行融资,目前监管也不是很鼓励,但仍然有合规的处理方式。”叶青表示。